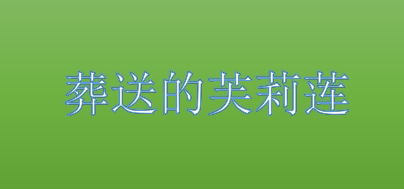by 乌合之子 20230711
毋庸置疑,在观影结束之后,我承认这当然是一部非常热闹且刺激的动画电影。
因为是科学想象,将原本不应该具备生命的交通工具拟人化为能说会笑的小孩子超级英雄,他们是超级飞侠,所以可以穿梭在天空之中。
 (资料图)
(资料图)
他们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同时具备着喜怒哀乐,这当然是一种泛灵论的观点,万物皆有灵,所以一定可以对话并成为朋友。
这比之于福瑞,更进了一步:动物的拟人,是有生命作为基础的;而机器的拟人,需要先对零件赋予想象。
只有大人才会去分辨有无生命,小孩子则全都要。
《超级飞侠》的受众到底是谁呢?
今天下午在进入电影院的时候,我发现周围坐着的全是妈妈带着女儿。这些小朋友虽然也会吵闹,但她们总会选择在某个特别的节点,那就是当超级飞侠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们会吵着对妈妈说,“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因为她们不忍心自己心中的一个完美的乐迪使出极限加速,让自己失控;也不愿意看到超级飞侠们在没有装备的情况下,面对坏人的袭击一筹莫展。
那么回到一种更加安稳的表现手法,就是动画剧集的完成任务的手法可以吗?
如果仅仅是像电视剧集那样完成每集的任务,不过是一个海螺小姐式的重复,因为对于孩子来讲每一天都可以完成全新的任务,送达包裹、解救危险、增长见识。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都可以将故事无限延伸下去,直到第14季。
但对于电影而言,可重复的任务反而成为了掣肘。所以一定需要讲一个更为漫长的故事,一定需要塑造出某种更加根本性的危机,以及更加绚烂的反派。
而反派最好就是大人。
那么在一个满是低龄向受众的动画电影中,如何为反派赋予一种可以说得过去的动机呢?一般而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诉诸于原生家庭童年阴影,正是因为小时候受到了霸凌长大之后才想为自己的过去正名;另一种则是诉诸于突如其来的时代挫折,原本是受欢迎的成年人,因为时代变化从此不再被关注,于是心生妒忌。
《超级飞侠》里,比利威利成为反派的原因正是后者。他所制造的玩具能给孩子们带来快乐,但是当网络流行开始之后,这些千变万化的玩具被千篇一律的画面所取代。
每个人似乎都在享受着由新技术所带来的新乌托邦的快乐:故事最开始不断玩手机的小男孩、在蝌蚪榜单中争先后的表演、不断实现创意视频的宇宙梦想家飞飞,还有随时可以跟踪拍视频的肖邦,他们都共同组成了像比利威利这样的玩具大师的生存困境。
这不值得可怜吗?比利威利就应该被抛弃吗?
也正如大卫格雷伯在《规则的悖论》中所说,超级英雄似乎从不创造任何事物。相比之下,大反派们坚持不懈地发挥着创造力,总是有一堆计划项目和想法。因为反派才是那个拥有着青春期、混乱创造的强烈渴望的梦想家。
所以我们便会问一个问题,沉浸在自己玩耍玩具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快乐,与不断分享和表演所获得的快乐,哪一种才是更好的呢?
这个问题在乐迪身上也得到体现。他如果专注于自己送达包裹的目标,他的情绪不受到周遭的影响,不会想要急于去证明自己,那么他就能够获得在这份工作中的快乐。
乐琪不是说:你能看到每个孩子收到包裹时的笑容,这就是幸福。可是这份笑容是私人的感受,不是能被人分享的。
可以被更网络化所分享的快乐,明显就是被异化辖制的快乐——作为世界上最快的飞机,乐迪没有办法在孩子们和网络的视线内表现他的超级速度,可以帮助多少人可以浇花,可以分类垃圾。却因为一段笨拙的被涂有五颜六色的痕迹,上了网站的热搜,成为了伙伴口中取笑的对象。
虽然动画在处理的过程中,很快将其转为了个人单打独斗比不上团结更重要的主题(这可是相当保守主义的处理办法),但是由互联网所带来的情绪改变,成为了超级飞侠们的嫌隙。
不过这份嫌隙,在新装备的帮助下消失了。因为他们又开始并肩作战,而不是排名表演。
借助更加先进科技的反派们,用一种近乎玩闹的方式搭建起了水火箭,他们成为了自己所反对的模样:不是用可触摸的玩具,而是用无法接触的高科技。
可是高科技就天然可以带来生命吗?
在将机械或动物拟人化的过程中,创作者必须要慎重表达如何区别对待有无灵魂的问题。
如果只有一部分同类型的物体,可以变成有灵魂意志的存在,那另一部分为什么不行?
同样的道理,如果在这一群体中只有几个角色可以大放异彩成为英雄,那其他人为什么不行?
孩子们会对这种差别心有所怀疑。
坐我旁边的小女孩,就在问她的妈妈:
为什么超级飞侠可以和人对话,而飞飞的妈妈坐的汽车,却不能变身,要在高速公路上堵车?为什么反派角色可以将自己驾驶的机械变成武装战斗机器人,而超级飞侠们却只有装备?为什么装备也不能参与对话?它们只能成为超级飞侠们的装备?为什么这些武装战斗机器人,没有灵魂、不能对话、无法沟通?
她的妈妈哑口无言。
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是欢迎这个小姑娘以后来读我们哲学系研究生。
就像飞飞的妈妈完全不理解蛙站的视频得奖邀请,为什么比奥数竞赛更重要?
是的,飞飞喜欢在网络视频中获得赞颂,内心的诉求依然是家庭式的,她希望早日和父亲(一家三口)见面,希望妈妈不要总是在外面上班,让她一个人落在家中,描绘的宇宙画面正是她想要团聚的景象。
这种设定相当取巧,把父亲的工作变成了宇航员。但实际上,父母都是受到996压迫的存在,所以这种焦虑才由妈妈传递给了飞飞。
而这种来自人类真实的亲缘家庭关系,对超级飞侠们来说当然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天然就是超级英雄——至于要不要吃“炒鸡”这种食物,机器英雄怎么能吃饭呢?那就也连带动画里的人也不吃吧。于是整个电影里,只有道格才塞进去了一块热狗。
吃是小事,死亡才是大事。
当乐迪献出自己的生命“以被摧毁”的牺牲精神阻止了水火箭撞向月球,电影院的孩子们全都哭出声来,一时间哭声此起彼伏,正好与这几分钟完全默片的画面相得益彰。
还有旁边妈妈们的劝说,乐迪不会死的,不会在太空变成无人看到的垃圾。但应该如何复活乐迪呢?
竟然是以谁都没有想到的方式——被肖邦的电流刺激。
这就又回到了那个问题,生命才会呈现出快乐,那么在网络上看到的排名是怎样的快乐呢?
网络为什么自身不能成为一个能喜怒哀乐的生命体呢?
这个故事,或许创作方奥飞能给我一个场外的答案:奥飞大幅度参与了ChatGPT的开发:
光年无限有自己的AI对话机器人产品-图灵机器人开放平台,开发者可自行快速接入并创建个性化机器人,包含聊天机器人、智能客服等,目前累计注册企业开发者超过150万。
所以,超级飞侠们是先是生命,才是机器。而现实正好相反,网络智能先是机器,才变成生命。
但就算变成生命,它也被褫夺了“说话的权力”,肖邦只能发出电流,接受指令——这当然是独属于飞飞的“超级装备”。
而那些“原始装备”去哪里了呢?
被乐迪混用之后消失了,去往了废弃的玩具工厂,去往了即将被碾为齑粉的垃圾场。
那里有曾经是孩子们快乐之源的玩具。